
改編至史蒂芬金小說的《牠》持續刷新北美九月份票房記錄,臺灣票房同樣大賣,引發討論熱烈。關於過往版本、小說比較或是小丑於恐怖電影再現形象同樣隨著話題討論紛紛出爐,本文就不再贅述。
我要就片中一些不甚被認為重要的點作討論:血與愛滋。
在Ben被惡少拿刀劃破肚皮時,他鮮血直流,而後因緣際會逃進樹林遇到主角四人組搭救。他們前往藥局想盡辦法要拿到止血醫療繃帶。進屋前,小孩們囔囔Ben可能會有愛滋害自己因此感染,愛滋很可怕。
只是幾句一閃即逝的台詞,卻顯示那個年代的愛滋恐懼。
別於小說原著,《牠》的故事設定在1989年。八〇年代愛滋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籠罩美國,將人們二元區分為陽性陰性,我們他們。愛滋病病例最早於1980年底至1981年初發現。起初這項疾病被稱為男同志免疫不全(GRID)而後更名為愛滋病(AIDS)。為了方便記憶,部分醫生劃分出四個危險族群4H,同性戀、海洛因藥癮者、血友病患者、海地人。這樣歸類危險族群而非感染行為的錯誤公衛知識很快造成反效果,非4H感染者在十年內快速攀升,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會感染。
美國知名雜誌Life於1985年曾把封面故事留給愛滋病危機,可以見得疾病對於當代美國的影響劇烈。假如你無法想像,可以觀看奧斯卡得獎電影《藥命俱樂部》或是紀錄片《那些年,我們在這裡》甚至今年底即將上映的法國電影《BPM》,都可以見到愛滋病對於歐美國家的衝擊。
愛滋病的蔓延,美國政府要負非常大責任。當時雷根政府袖手旁觀,直至1987年雷根才公開談及此話題,那時候,美國愛滋病已經奪走兩萬條人命,報紙每週滿滿訃聞,人們提心吊膽閱讀報紙,得知身旁摯友死去。雷根總統演講撰稿人曾公開宣稱:「性革命在殲滅後代,愛滋病是自然界對企圖違反規律的人進行報復」,這番保守派天譴論加劇愛滋污名傳播。
不也難怪,《牠》這群緬因州小孩對於愛滋病的恐懼會如此強烈。
暫緩愛滋議題,將「血」的議題帶到女主角Beverly身上。Beverly的恐懼源自於父親性侵以及青春期的身體成長(經血)。因此小丑為激發其恐懼感令她浴室灌滿鮮紅血液。
這幕令人不自覺聯想到史蒂芬金經典改編電影《魔女嘉莉》。女主角嘉莉發現經血後魔力覺醒以及在舞會中被女反派惡整倒滿全身豬血導致發憤失控屠殺校園。學者Barara Creed結合Kristeva的精神分析概念作出的恐怖片的理論性閱讀,《魔女嘉莉》是她的其一文本分析。她認為恐怖片將母親形象建構為賤斥(abject)。在人類文化中,賤斥形象與母親有關,特別是經血。這種污染是特別的,代表秩序的分裂,區分出母親的權威與父權的律法。這些「穢物」威脅著一個完整統合主題(父權)所以令人厭惡。
將論點帶回《牠》審視。因為父權(男性暴力)導致,賤斥符碼「血」再次出現於史蒂芬金電影當中,象徵著主體社會對於Beverly的排斥。如同男孩母親對Beverly的口出諱言:「妳做的骯髒的事我都知道」。除了血的符號,Beverly更是一名遭「賤斥」的人體。她被認為擁抱情慾恣意與男人上床不被這「女人不能談性」的父權社會所接受,因而受到排斥。
同理延伸,愛滋病、感染者亦被健康至上的父權社會所排除。
有趣的是,「血」的意象卻在電影最後反轉。小孩們相約二十七年後保護小鎮。彼此以玻璃劃破手掌,流著血液的手掌互碰緊握做出血誓盟約。劇末曾點出小丑的力量來源:恐懼。小孩們了解到唯有不再懼怕團結面對才能打敗小丑救出Beverly。電影沒有明說,但男孩們劇初的愛滋「恐懼」卻在這個時候破除了。孩童們信任彼此,瓦解愛滋恐慌,以致敢於用血手互握。
這點證明愛滋污名是可以破除的。只要你願意理解,「恐懼」就能夠消滅。現在已是2017年代,愛滋病早已能夠透過藥物穩定控制,壽命與非感染者無異,外觀亦沒有差別。只要了解傳染途徑,不做出高風險行為,就不會感染HIV病毒進而可能病發AIDS。
然而醫療知識發達的臺灣,某些團體卻利用著愛滋病持續污名某些特定族群,宛如《牠》的小丑利用恐懼獵殺兒童。官員的錯誤知識點出「危險族群」而非「危險行為」,更是強化特定族群的被排斥感以及給予大眾錯誤知識。
如同男孩們集結勇氣面對恐懼救回Beverly;
我們也應當面對愛滋,不再讓恐怖小丑繼續利用著「恐懼」獵殺無辜群眾。
延伸閱讀:〈愛滋電影專題:汙名依然存在〉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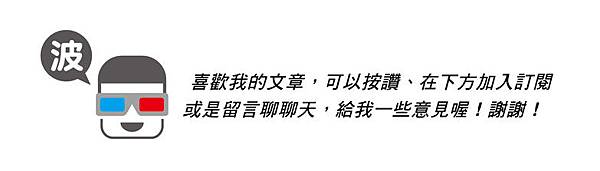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